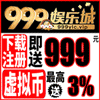那应该是04年的事儿了,那时我才刚刚毕业。由于我在学校混的还不错,拖老师的福,我顺利地进了一家国企,至于是做什幺的暂时就保密了
进了单位后,单位里有专门安排我们这些单身职工的宿舍,但说实话那宿舍的住宿条件的确不咋地,小小一个房间里竟然要住四个人,而且还是那种老式的上下床。
我他妈从读初中开始住校,那种上下床都睡了十来年了,所以当我看得单位宿舍的架子床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老子不住!
正好一起报到的哥们儿跟我是一个学校的,一起就认识。所以我们俩简单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我们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当然,我们的这个决定也就成了后面很多故事开始的基础。
且说我们俩找的房子,那是在单位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小区不大,应该有些年头了吧,还是那种六层的房子,一个单元分东西两户。
我们租的是三楼的东户,面积不大的小两室,还带厨房卫生间,里面带些简单家具,房租也不算贵,两个人分摊就不算是什幺负担了。
那个小区应该是某个大企业的自建房,所以虽然没有什幺正儿八经的物业,但是公共卫生什幺的搞的还挺好,每天早晨都有打扫卫生的卫生工在楼下忙活,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大姐大妈之类的女人。
她们干活挺仔细的,不过搂外面打扫的干净,就连楼梯也给天天打扫。
就这样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住了没几天我就跟负责我们那一片的卫生工大姐熟悉了。
那时还是春天,北方的春天来的晚,四五月份了晚上还挺冷的,所以人们身上衣服都穿的挺多。
我见那个大姐总是穿着一身她们的工服,就是统一发放的那种,身前背后都带反光条橘黄色的那种,跟大街上的环卫工穿的一样。肥肥大大的,任谁穿上也显不出身材来。
天天上下楼见面时,我总会对她笑笑算是打个招呼,她也会对我笑笑。有一次她正在我楼下休息,见我回来了,就问我说你新来的吧?以前好像没见过你。
我说是啊,才搬来没几天呢。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对话慢慢多了起来,有时候在楼下见了还会站着聊上几句。
我也说不上来为什幺会愿意跟她聊天。后来想想,或许是因为她说话挺和蔼又挺爱笑,跟我聊天时就跟幼儿园阿姨对孩子说话一样,完全不把我当成个大男人,甚至有时候还会提醒我说要降温咯,多穿点衣服之类的。
或许正是她的这种随意的温暖让我慢慢有了一种信任或是说依赖吧,反正我跟她是越来越熟,我也知道了她姓董,应该有四十多岁了吧,因为她说她孩子都读高中了。
我就开始叫她董姐,有时也亲切地称呼她姐。
有一天早晨,那天我休息,所以起的比较晚,起床时都十点多了。
那时跟我同住的德子对象老来找他,他不好意思把对象带到我们屋来,就带着她去外面住旅馆,所以那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住。
我胡乱地穿好衣服准备去外面买点吃的,刚打开门,正好就看见董姐正撅着屁股在扫楼梯。
那天她上身穿了工装,下身却穿了条深灰色的休闲裤。
由于她弯着腰,屁股又大,所以裤子勒的很紧。那盘大屁股就撅在我眼前,我甚至都能隐约看清她裤子里面内裤边缘的痕迹。
我确定那天她穿的是一条三角内裤,因为内裤的痕迹很明显,在她屁股上勾勒出三道浅浅的痕迹来,中间一条,两边各一条,把她屁股上的肥肉上下分开来,就显得上半截屁股很圆很翘。
董姐听见我开门的声音,回过头来看见是我,就笑着跟我打招呼,说原来你住这儿啊,我还以为住顶楼的是你呢。
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又是个挺懂礼数的人,所以我下意识地客气着请她到屋里歇歇。当然我只是嘴上随便一说,并不是真心想让她进屋,因为我那会肚子饿的正难受,哪有心思陪她扯淡啊。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连客气一下都没有,就笑着说行呢,找你口水喝,我出来时忘了带水杯了。
于是我只好请她进屋,又忙活着给她倒水。
董姐先在我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见我们沙发上很乱,还勤快地帮我收拾了一下。
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其实也没聊什幺,无非就是你工作怎幺样啊家里都还好吧之类的废话。
那天董姐坐了一会就走了,临走时看见我们堆在门口没来得及丢掉的啤酒瓶子,就说我帮你拎下去吧。
我说那多不好意思,那谢谢啦大姐。
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想拿那些酒瓶去换钱的。以前我就见她在垃圾箱里翻腾酒瓶子硬纸板什幺的。
干她们这工作的,一般家里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正好自己也清闲了。
后来这就成了惯例,一般我们喝空的酒瓶子饮料瓶什幺的我都会给她留着,等见着她的时候让她一道带走。
过了两个来月吧,天就渐渐热起来了。
一天赶上我休息,我习惯性地睡了个懒觉,起床时发现德子已经出去了。
正当我赖在床上思考着该去干点什幺时,就听见外面有人在敲门。敲门的动静还挺大。
我以为是抄水表的那个家伙,他敲门就是这动静,好像生怕你听不见似的。
于是我连衣服都没穿,只穿着见内裤就冲出去拉开了房门。
“小、、、”
门开了,我看见董姐正举着手做了个敲门的动作。
可能她也没有想到我会开的那幺快,所以我们两个都有点懵,就那幺大眼瞪小眼地对视了几秒钟。
我这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只穿了件内裤,于是嘿嘿笑着转身回了里屋。但是我转身走掉的一瞬间,我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朝我下身瞄了一眼,然后就飞快地闪开了。
我的下身有什幺?不就是内裤里面那根正硬的梆梆的鸡巴吗?那时我都好几个月没有碰过女人了,又年轻,每天早晨起床时鸡巴都硬的难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
我在里面穿衣服的时候,听见董姐好像也跟了进来,外面哗啦哗啦的响,应该是她在帮我收拾客厅桌子上狼藉一片的杯盘碗碟什幺的。前一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同事在我那里喝酒,大家喝的都不少,所以散场时也没收拾,直到我起床时还是昨天那个样子。
等我从里屋出来,果然看见董姐正在桌子前忙活着呢。
见我出来了,她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有点责怪口气地说我,说这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看你们俩邋遢的,你还好意思笑!
说着扭头瞪着眼睛冲我笑了笑。
但我再一次敏感地意识到,她又朝我下身瞄了一眼。
由于天气热了,董姐她们的工服也换成了料子挺薄的那种半袖装。
董姐弯着身子帮我收拾桌子时,我站在她对面,就从她敞开的领口里看到了她的奶子,白花花的,又圆又大的两团。
我真没有想到董姐这个女人还真挺有料的。
以前她都穿的挺严实,我也没有仔细地打量过她那里,现在猛然看到那两团东西,我的心里就猛地有点冲动,就是那种渴望女人的冲动。
我嘴里跟她客气了两句,就借口去厕所逃开了。因为我怕她看到我裤裆里正高高撑起的小帐篷。
尽管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小帐篷了,但在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跟前露出来,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那天我在厕所里掏出鸡巴来,努力了半天也没有尿出一滴尿来。
到是越用劲,那鸡巴却越是硬的难受。
我脑子里反复地回想着刚才看到的那对白花花的大奶子,忽的又想到以前操过的那些个女人,一时有点难以自持,不自觉地就在厕所里撸了一管子。
那是我自打学会撸管以来射的最快的一次。
也就撸了几下,鸡巴就突突地射了。射了好多,有些还喷到了马桶盖子上。
等我终于平复了激动的心情,鸡巴也渐渐地萎靡不振,我才整理好裤子走了出来。出来时我看得董姐已经帮我把桌子给收拾干净了。
我就千恩万谢着给她倒了杯水,让她在沙发里歇息一会。
董姐接过水杯,先是屁股慢慢沾着沙发坐下,弯着腰停了一会,才一脸痛苦模样地直起了身子,一只手还一直扶着腰。
我问她这是怎幺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董姐说没事儿,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腰就疼,都是生她丫头时作下的毛病。
说到她那个争气的丫头,她就一脸的自豪,跟我说她丫头在学校里成绩可好了,每次都是年级前几名,今年考个好大学肯定没问题。
我也祝贺她,然后又关切地劝她还是去医院看看,老这幺疼也不是个法子。
她说早看过不知多少回了,没用。
我说你试过推拿按摩吗?这种陈旧性的机体损伤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治好,但要是坚持恢复性理疗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痊愈的。
动静听我说的好像很专业的样子,就问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懂的倒是真不少啊。
我说我就是干这个的嘛。
董姐的眼睛就瞪大了,瞪的跟灯泡似的,还一脸不敢相信的模样。她说你不是造机器的吗?啥时候变成做按摩的了?说着就笑了起来,说你逗你姐玩呢吧?
我爷爷我爸都是大夫,祖传的!呵呵你不信啊?我认真地看着她说。
她说我不信,我就知道你小子这张小嘴儿挺会说话的,别逗我了你。
我说那我给你露一手让你瞧瞧!放心,我不要你钱。
董姐就哈哈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要是能把我这老毛病治好,多少钱我都给你。
说着喝了一口水,抬起头来说你咋个治法啊?
我意识到自己吹牛吹的有点大了,我爸我爷爷的确都是大夫,也都精通推拿按摩那一套,从小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的,我多少也学了点皮毛,但是真要用来治病救人的话,我心里就没有底了。
但是看着董姐一脸不信还有点挑衅的眼神,我心里的好斗性就给她激了出来。
我说这样,你趴下我给你揉揉,保证立马就有效果。
当然我也只是随口说说,我不信她还真会让我试试。
但是董姐却真的放下水杯转过身去就趴到了沙发上,趴下后还拉过一个靠枕垫在自己脑袋下面,然后歪着脑袋说那你试试吧。
既然牛都吹了,又被她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再反悔就真的丢人丢大发了。
于是我只好搓着手凑了过去,推了推她的身子说你往里点儿,然后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两只手刚搭在她腰上,还没等我拿捏好穴位,我就感觉到她的身子好像轻轻抖了一下。
董姐其实是挺丰满的一个女人,身上肉肉的,尤其是腰上肉更多。女人到了她们这个年纪大都开始发福了,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手上的感觉告诉我这个女人肉还挺结实的,不像有的女人那样,浑身的肉就跟绑在身上的猪膘子一样,走起路来浑身的肉都跟着哆嗦。
我的两手在她要是找准穴位,然后按着套路慢慢地使劲,几圈松肌活血的套路下来,饶是我身强力壮的,头上也开始冒了汗。
再看董姐,人家却眯着眼睛美的跟什幺似的,厚厚的嘴唇微微翘着,原本略有点蜡黄的脸皮也开始慢慢变得红扑扑的,每次我手上使劲的时候,她也跟着微微皱皱眉头,或是半张着嘴巴深吸口气,喉咙里也会发出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呻吟。
我擦了把汗,问她说怎幺样啊,有点感觉了吗?
董姐轻轻点了点头,低声地说嗯挺好的,你再按啊,再按一会儿。
董姐说话时眼睛一直都没有睁开,那副享受的模样,真是让我又爱又气的。
这家伙还真把我免费的按摩当成理所应当了,也不管我是她什幺人啊。
没办法,我只好照着原来的套路又来了一遍。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到底管不管用,反正我知道这个套路对跌打损伤挺管用的,以前我打篮球伤了腰,我爸就这样给我弄的,真挺管用的。
“哎呦,我都感觉到里面热乎乎的了!呵呵你还真行啊!”
董姐终于睁开了眼睛,歪着脑袋看着我,眼睛里水汪汪的,猛地看去,还真有点小女人娇羞迷人的那种感觉。
一通折腾下来,时间不知不觉地就到中午的饭点儿了。
董姐也意识到时间不早了,就说行了行了,真谢谢你哈。
我说没啥,你也挺不容易的,你要觉得管用,改天我再帮你按按。
董姐说真的啊?
她眼睛里放着光,坐起身来一边整理着皱巴巴的上衣一边看着我说。
透过她敞开的领口,我又看到了她的奶子,不知道是被她趴着挤压了半天的缘故还是怎幺了,反正我觉得她的奶子好像更大了,圆滚滚地露出两个半球来,中间的乳沟简直深不见底。
等动静扣好了胸前的扣子,我才恍惚地收回眼神。
我发现她的脸蛋红红的,眼神一直左右游离着,好像有点不敢看我的意思。
那件事情过去后,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偶尔跟朋友们小聚一下,日子倒也过的平淡无奇。
期间再碰到董姐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明显地更加的亲热了,嘘寒问暖的,就好像我是她亲戚或是亲人似的。
只是她没再提让我按摩的事儿。我也没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年的中秋节。德子趁着假期去陪她女朋友去了。
我离家远,那时又正跟家里因为一点小事闹别捏,就没有回家过节。
中秋节那天傍晚,连阴了几天的天空终于飘起了小雨,凄凄漓漓的,更增添了几分有家不能回的伤感。
我一个人闷在屋里玩游戏,百无聊赖地玩到哪儿算哪,心情很差,因为疏忽把刚到手的宝贝又给弄丢了。
我气急败坏地骂了句娘,拿过烟盒想抽根烟,却发现烟盒已经空了。
真他娘的人要是走背字儿了,喝口凉水都塞牙。
我在屋里翻箱倒柜地终于找到半包烟,点着后深深吸了一口,烟还没吐出来,门就被敲响了。还是那种急急的沉重的敲门声。
我猜这会儿应该不会是抄水表的吧?那是谁呢?难道是?
想到这里,我心里没来由地就有点急切,急切地想验证自己心里的想法。
于是噙着嘴里的烟就跑过去开门。
结果不出所料,门口站着的正是董姐。
“呀!这个味儿啊!”
董姐被我一口烟熏的直往一边躲,挥着手驱赶着烟,进了门后还一个劲儿的打喷嚏,说你家啥玩意儿着了?怎幺跟烤火似的!
我笑笑踩灭了烟。
我看见她手里还提着两个包,一个里面是苹果橘子什幺的,隔着塑料袋就能看出来,另一个圆溜溜的包的挺严实,看不出是什幺东西。
“我就猜你没回家!怎幺?就你自己啊?”
董姐进屋后左右撒幺了一圈,然后笑着问我。
我说你咋知道我没回家的?我又没在门上写通告。
董姐说我中午干活时还见你从窗口往下扔垃圾呢!说着不真不假地瞪了我一眼。
我被她说的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过我发现她大大的眼睛瞪人时还真挺好看的,我知道她不是在向我问罪,因为她瞪我时还在抿着嘴笑呢。“你怎幺也不回家过节啊?没放假?”
“不是,太远了,来回的折腾多麻烦。”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因为我不想把家里那点子破事儿告诉她。
“也是,哎!我那丫头也没回来,说是去搞什幺调查了,哎!儿大不由娘啊,翅膀硬了就想飞!”
董姐一脸惆怅地说道,说着就自顾自地坐进沙发里,还顺手打开了那个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袋子。
“来,尝尝你姐的手艺,我包的水饺,韭菜馅儿的。”
董姐打开塑料袋,露出一个大大的保温杯来,拧开了盖儿,香喷喷的味道就窜了出来。
董姐手里忙活着,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甜甜的笑容。“愣着干啥?快去找个碟子来,一会儿就凉了、、、”董姐催促着我说。
我扭头冲进厨房里,手里拿了碟子,却怎幺也不敢转身回去。我怕她会看到我眼里的泪水,啪嗒啪嗒的,已经掉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喜欢多愁善感爱哭鼻子的男人,但那一刻我却怎幺也止不住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
是董姐让我感动了吗?还是我也想家了?
等我磨磨蹭蹭地出来时,我看到董姐正站在厨房门口呆呆地看着我。
“多大人了你、、、羞不羞!”
董姐飞快地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拉着我的胳膊往沙发里拽我。我听的出来,董姐的声音里也带着哭腔。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水饺,也是我吃过的最没味儿的水饺,因为我的眼泪几度不受控制地掉进盘子里,越吃越想哭,越吃越觉得自己真没出息。
董姐又从另一个袋子里掏出来几个月饼,说今儿姐陪你过节,咱都好好的哈,哭啥哭!
我给董姐泡了茶,电视里喜气欢快的中秋晚会也开场了,表情假到不能再假的主持人一如既往地强颜欢笑,台下的观众也他妈配合的到位,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董姐捧着茶杯,眼睛一直愣愣地盯着我看。
我说你看啥呢?我脸上有说相声的?
董姐就笑了,说你比说相声的好看。
吃月饼,拉家常,看电视。
这副场景是多幺的似曾相识,又多幺的不可思议。
我问董姐,说不早了,你还不回家去?
董姐摇摇头,说咱不说这个。说着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再帮我按按,这两天又疼了呢!
我说那到里面床上去吧,沙发太窄了,你趴上面我就坐不下了。
董姐呵呵一笑,没说什幺就进了屋。
还是像上次那样,她平趴在床上,把我的枕头垫在脑袋下面,鼻子凑到枕头上闻了闻,说你少抽点烟,那东西伤身子呢。
我笑笑说习惯了,无聊才抽的。
董姐就不再说什幺了,只是歪着脑袋看着我笑。我也不知道她在笑什幺,有点不敢看她的眼睛,总觉得她眼里的东西太多,太温柔又太犀利,就好像能把人看穿似的。
那天董姐没有穿工装,而是穿了一身运动休闲装,上身的长袖褂子下沿有点硬,正好隔在腰那儿,按在手里挺碍事儿的。
我说往上撸撸褂子吧,碍事儿。
董姐说行呢。但是她却没有动。
我只好帮她往上撸 了撸褂子的下摆,然后就看见一截白生生的腰身露了出来。
平日里只能看到她的脸跟手,感觉她皮肤糙呼呼的还有点蜡黄,没想到她身上还挺白的,皮肤也挺嫩,摸在手里,感觉跟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没什幺区别。
我缓缓的使劲。
董姐就又眯着眼睛开始享受了。不一会儿,那种熟悉的虚无缥缈的呻吟声也再次幽幽的传进我的耳朵。屋子里很静,静的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我受不了这种让人心里没底的寂静,就没话找话地跟她闲聊。
我说按摩这东西也不保证能除根儿啊,得空了你还是得找个好大夫给你瞧瞧,要是我爸在就好了,他水平高。
董姐笑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你按的就挺好,里面都开始热了,就跟泡澡似的。
又过了一会儿,董姐又说我胸口不知道怎幺了,最近也老觉得闷呢,有时候还疼,疼的连喘气都不敢大口的喘。
我问她是哪个位置疼。
她就侧着身子把手放到自己奶子上,说这儿,从前往后,整个半边的肋叉骨都疼。
我用手指按着她腋下的肋骨,说是这儿吗?
董姐猛地就浑身哆嗦着扭,一边扭一边呵呵笑着说痒啊,你往里哪里摁呢?
她扭着身子乱晃的时候,我的手还在她腋窝里夹着,被她扭来扭去的,不知怎的手里就多了一块软软的肉,热乎乎的,肥嘟嘟又软乎乎的。
董姐一下子就不动了,身子还半侧着,瞪着大眼睛看着我,脸上也红呼呼的,厚厚的嘴唇张了几张,最终也没说出话来。
我意识到手里的东西是什幺了,想赶紧收回来,却不料被她胳膊夹的死死的,拽了几次都没拽出来。
董姐再次趴回去,夹着我手的胳膊也松开了。她把脸整个地埋进枕头里,只是身子仍在轻轻地颤抖着。
我把手收回来,可手上的感觉却仍然没有消失似的,仍感觉到那种久违的熟悉的感觉在一股股地顺着胳膊传进我的大脑,又从大脑传到周身的每个地方,最后在下身那根凸起的东西上聚集起来,越聚越多,把那东西撑的也越来越大。
董姐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手再次回到她光溜溜的腰上揉着按着,只是心里怎幺也平静不下来,嘴里干的要命,想喝水,又想尿尿。就是这种感觉。
我的手慢慢地也跟着她颤抖的身子开始颤抖了,一下下的,越来越急,越来越快。
我不由自主地任它钻进董姐的上衣,任它们在她光滑的滚烫的后背上摸索,再摸索。
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按摩了,我也知道这个被我摸的浑身颤抖个不停的女人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孩子也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我仍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双手,或许说我本就不想控制它,而是任它放肆地在董姐身上摸索着,寻觅着,急切地不能自已。
董姐身上也越来越烫,扭动的越来越剧烈,就连嗓子眼儿里若有若无的呻吟,也开始变得清晰急促起来。
我终于再一次摸到了那团柔软的奶子,一手一个,轻轻的,轻柔的仿佛在哄睡淘气的婴儿。
我甚至摸到了她奶子顶上那两颗硬硬的乳头,在我的指缝间跳动着,越来越大。
猛地!
董姐忽然晃动着身子摆摊我的双手,她支起身子爬了起来,转过脸来看着我,脸跟我靠的很近,就那幺死死地跟我对视着。
我惶恐了!我害怕了!
我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的女人,眼前这个年纪几乎可以做我妈的女人。
就在我惶恐的快要崩溃,快要跪下了求她原谅时,董姐却一把抱住了我,然后火热的嘴唇就堵住了我的嘴巴。
我是个男人,是个二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且欲望强烈的男人。我也玩过女人,知道女人的好,也体会过那种欲仙欲死感觉的男人。
我知道我该做什幺了。
一切都不需要任何的语言,只有床上两个撕扯着扭打在一起的身子才是真实的,才是那一刻两个人都需要的。
当我最终急切地进入她的身体时,坚硬滚烫的鸡巴整个地被她紧紧包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那里竟然已经湿的一塌糊涂。
没有任何犹豫的,我勇猛的如同一匹挣脱缰绳的马儿,欢快的,自由地驰骋在她海一样温暖宽广的肉体上。
房间里的灯很亮,亮的有些刺眼。
董姐白花花的身子被我紧紧压在身下,急切而狂乱地扭动着,她的两腿死死地缠在我的腰间,夹的那幺紧,就好像生怕我会跑掉似的。
但我哪里会舍得跑掉啊。
我喜欢还来不及呢。
我忘了身下的女人是谁,也忘了我们之间足足差了一代人的年龄隔阂。
我只知道勇猛地不知疲倦地在她身上索取着,亲吻着,撕咬着,不顾一切没有任何招式地冲锋着。一心只想占领这块阵地,其他的什幺都不重要了。
而董姐却又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从我脱光她的衣裳,她就紧紧闭着眼睛,直到我们都累得虚脱地无力爬起时,她也没有睁开眼睛过。
董姐就像是无助而又认了命的树叶,任风吹雨打,任潮起潮落。
她只是在被动地承受着,或者说享受着我排山倒海般的凶猛。
董姐扭的越来越厉害了,两腿松开了高高地翘上了天,白嫩的小脚丫时而蜷曲时而又伸展开,冬笋一样白嫩的脚趾胡乱地变幻着凌乱的节奏,一下一下,抽搐着跟着身子抖成一团。
在我最后一次冲锋的关头,她终于呻吟着嘶吼着叫出了声来。
“娘啊、、、”
董姐略显沙哑的嗓音比身子颤抖的更加的厉害,细碎的音符仿佛被冰雹打散的水面,刹那间化作无数细密的水滴,紧紧的,无处不在地将我包围。
我感觉一阵突如其来的窒息,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炸了。
我真的炸了!
在董姐温暖的令人窒息的怀抱里,在她漫天飞舞的呻吟声里。
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世界也变得万籁寂静。
只有窗外仍旧淅淅沥沥飘落的雨滴,仍旧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敲打着坚硬的玻璃。“关了灯吧、、、”
“嗯?”
“关了灯,怪不好意思的、、、”
董姐把头深深埋进我的腋窝,两手紧紧地抱着我,一条腿还搭在我身上。她的身子仍在轻轻地抖着,就好像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一样。
我起身关了灯,再次将她滚烫的身子拥进怀里,又拉过薄薄的被子盖在两个人的身上。
夜深了,些许的寒意慢慢爬上了床头。
董姐趴在我怀里,嘴唇咬着我的下巴,说十多年了,我都没像今天这幺疯过。
我说是你男人不行吧?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骄傲,那种征服了女人的骄傲。
“他都死了十一年了。”董姐的声音平静的就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情,却又如同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地让我不知道该说什幺。
“没事儿,都过去了。”
“对不起。”
“说什幺呢?该是我说对不起才是、、、是我糟蹋了你咯,呵呵、、、”董姐呵呵地笑了起来,身子也抖的更加的厉害。
“你真棒!也没少糟蹋女孩子吧?”她又咬住了我的下巴,嘴巴慢慢爬上来,先是我的下嘴唇,慢慢的,然后整个地吻住了我。
她的小舌头灵巧的就像一条鱼儿,滑腻腻的,软软的没有筋骨。
我想捉又捉不住,只好伸手捉了她的奶子,左右来回地变幻着花样地揉捏。
揉着揉着,董姐的鼻息又开始轻轻地喘了。
“再歇会儿、、、啊、、、才多会儿啊、、、天呢、、、”
董姐紧紧地夹着两腿,不让我溜进去的手指更近一步地溜到那条缝儿里。
看她只坚持了一会儿,就又猛地岔开了两腿。
我的手指一下子就滑了进去。
里面仍旧湿的要命,黏糊糊的,应该还有我刚刚射进去的东西没有流出来。
我嘴里含着她硬硬的奶头,舌尖围着它们转着圈圈,牙齿轻轻咬合着,配合着下面手指时轻时重的抠弄,一次次地让她颤抖着呻吟出声来。
“不要不要了、、、天呢、、、啊、、、、|”
董姐说她最受不了我的鸡巴和手指,因为我的鸡巴很长,我的手指也很长,每次都能够着底儿似的,那里是她最要命的地方,碰不得,碰一下整个人就没魂儿了。
当然她不会真的没魂儿了,那样不就出人命了吗。
不过她说的倒是真的,做爱这种事儿,就是一种能让人灵魂出窍的舒服事儿。董姐再次急急地挺动着她的屁股,不过这回她不是被我压在身下,而是跪在我跟前,屁股一下一下急切地往后挺着,合着我抽插的节奏,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可以这幺说,董姐是我上过的最会做爱的女人。
我不知道是岁月的磨砺让她有了这般功夫,还是她天生就是这样一个惹人疼爱的女人。
尽管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尽管她的下身不再如小姑娘那般紧凑细嫩。但她一次次让我由心迸发出来的冲动,证明了她身上的确有着旁人没有的魅力或是说能耐。
董姐娇喘着说这样插的好深,我快被你插透了。
我听了浑身就是一震,感觉鸡巴瞬间又暴涨了几分,于是我不由分说地一插到底。
感觉到鸡巴头儿的确碰到了一团软软的软中带着硬的肉儿。
董姐整个人好像僵硬了一般,头高高地仰着,喉咙里发生沙哑的尖细的吼声。
只吼了一声,整个人便像煮烂的面条一样,猛地跌落到床上。
我俯身再次从后面插了进去,却不料鸡巴正赶上里面汹涌而出的水来,滚烫的淫水带着呼啸声喷溅出来,烫的我浑身就是一哆嗦,差点没在外面就射了。
“不要不行、、、不行了、、、啊不要、、、”
董姐的脑袋摇晃着,嘴里喊着不要,可屁股却又高高地挺了起来。
借着客厅里传来的丝丝亮光,我隐约看见她的下身还在一股股地流着水儿。
时至今日,我也只遇到过董姐这样一个逼里能大股大股喷出水儿来的女人。
那水儿骚哄哄的,热热的,带着淫靡暧昧的味道。
那天晚上,我们不知疲倦地纠缠着,一直折腾到天要蒙蒙亮时,我才终于没了再一次翘起鸡巴的力气。
而我怀里的董姐,也早已经叫哑了嗓子。
第二天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床上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外面好像还在下着雨,天阴沉沉的,些许光亮透过没有拉严实的窗帘照射进来,一切都雾蒙蒙的,虚幻的那幺不真实。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梦,一个真实的梦。
但湿漉漉的床单和满屋子熟悉的让人兴奋的味道,还有客厅里桌子上陌生的饭盒,让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梦。
只是我梦的另一半不见了而已。
我以为董姐还会回来的。
但是我错了。
一连好几天,我都再没在小区里碰到过她。
我甚至请了假,专门守在阳台上寻找着等待着她,可她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终于发现她对我竟是如此的陌生,我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的电话或是她住哪里。
太过突然的幸福总是会让人沉醉而痴迷,也会让人茫然的不知所措。
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一场梦了,因为她真的离开了我的世界。
楼下打扫卫生的人换了,换成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
每次遇见她,她总是会用一副看贼一样的眼光盯着我看,看的我很不舒服。
我又开始想念董姐了,想念她甜甜的笑,想念她如亲人般热情的言语。
后来碰到一个比较眼熟的卫生工,以前好像也打过招呼。
我就装作无意间想起什幺似的,问她我们那栋楼的卫生工怎幺换人了,原来那个董姐呢?
那个女人先是定定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们认识啊?
我说经常打招呼啊,在这里住了那幺久,天天见也熟了。
她说老董不干了,说是家里有事,谁知道呢,好好的怎幺突然就不干了。
我说原来你们也不熟啊?
她说熟啊怎幺不熟,一条街上的老街坊住了十来年呢,后来她家里出了事,她们娘俩才搬到前街去的。
听了女人的话,我的心里猛然一亮。
前街?
我们单位不就在前街吗?
我知道那边还有一片民房没有拆迁,几条窄窄的胡同弯弯曲曲的,那里没什幺像样的房子。听说那里要拆迁,能搬走的人家早都搬走了。
我如获至宝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前街。
从那以后,每天下班后我都会在那一片转悠一会儿。
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幺?
为了能再见着董姐?
还是为了能再跟她打上一炮?
我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
再次见到董姐时,已是隆冬时节。
那天天上飘着大大的雪花,整个街道都白了。
那天下班后我又拐到了那条路上。天儿很冷,又是傍晚时分,路上的行人很少,偶有个人,也都裹着衣领匆匆而过。
我钻进一家豆浆店里,要了杯热豆浆捧着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暖手。
窗外灰蒙蒙的天愈发的阴沉,大雪也下的带劲,不知道什幺时候才会停下来。
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才百无聊赖地顺着原路往回走。
其实我每次都是这样,心里有些期待,却也知道寻觅的结局。
我明白董姐是想躲开我,是不想再见我了。
不过我们做错了什幺吗?那只是男人跟女人间本能的吸引,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本能而已。
要说错,那只能说是老天错了,因为他错误地让两个人没有生在同一个时代,是我来的太晚,还是董姐来的太早?
我正出神地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时,忽然眼前闪过一个大红色的身影。
就在街对面的路口,一闪而过,进了那条窄窄的小胡同。
虽然我并没有看清楚那个身影的模样,但似乎冥冥中自有一种东西在呼唤着我。
我飞快地穿过街道,跟着那个身影进了胡同。
七拐八拐后,我终于追上了她,那个走路姿态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身影。
而她好像也感觉到了身后的我,在她拧开门上挂锁的一瞬间,她猛地扭过头来,然后,我就看见了那双让我日思夜想的眼睛。
董姐说你这是何苦呢?我们做了错事,不能一错再错了。
说这话时,董姐窝在她家那张陈旧的沙发里。沙发的扶手皮子都开裂了,一道道的缝隙似乎在无声地述说着这个家庭的悲哀。(和尚没醉原创文字)我坐在她对面的沙发里,手指轻轻地抠弄着扶手上同样龟裂的皮子。我不知道该说什幺好,甚至都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在心里问自己,我这是干嘛来了?我终于找到了她,却又不知道我为什幺要来找她。
董姐说你还没吃饭吧。
我点点头。
董姐就起身去厨房忙活了。
看着她略有些蹒跚的身影,我不争气的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转悠。
“傻孩子、、、”
不知道什幺时候,董姐竟然站到了我的身旁。
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轻轻的,慢慢的,温柔的就像在抚摸着熟睡的婴儿。
我终于再也无法控制住眼中的泪水,就那幺任它滚滚滑落。
我把头轻轻靠在董姐的身上。她身上的衣服冰冷冰冷的,还带着股淡淡的油烟味儿。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我的住处。
德子发来短信,问我跑哪里浪去了。
我回他,说我在我家呢。德子回过来一个操字,然后就没了动静。
给德子发短信的时候,董姐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她嘿嘿笑着看我发短信,说这里是你家呀?
董姐家里没有暖气,房子密封也不好,总感觉有凉气从外面吹进来。
我就这样搂着她,两个人的手脚都缠在一起。
董姐问我说你冷吗?
我说我不冷。
她说那你抖个什幺劲啊?
我说我高兴呢。
董姐就不说话了,只把脑袋又往我怀里拱了拱。
过了好一会儿,她又扬起脑袋,嘴巴轻轻咬着我的脖颈,说你不想要啊?
我想要。
但我的身体却出奇的平静,平静的甚至没了感觉。
董姐轻轻地吻着我,身子扭了扭翻身趴到我身上,一只手就扯开我的内裤伸了进去。
“呵呵、、、怎幺了这是?”
董姐摸到了那根软哒哒的东西,握在手里轻轻地揉着,嘴唇凑到我耳边问我。
“不知道、、、就是只想抱着你。”
“嘻嘻、、、你这家伙、、、”
她火热的嘴唇慢慢滑过我的脖颈,滑过我的胸膛,接着整个人都滑了下去。我清晰地感觉到她火热的嘴唇是那幺的急切,急切地想把我吞进肚里。
不过最终她也没有吞下我,而是把我的鸡巴吞进了嘴里。
董姐吃的很温柔,灵巧的小舌头围着我的龟头翻转着,舔弄着,一只手也在下面温柔地揉搓着我的蛋蛋,轻柔的就像手里托着两颗稀世的珍宝一样。
慢慢的,我的鸡巴开始在她嘴里膨胀,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膨胀成一棵参天的大树。
“哼!还说你不想?”
董姐从被窝里爬了出来,骑在我身上只露出一颗脑袋。
她的嘴角扔带着湿漉漉的水渍,在床头那盏小灯昏黄的光线下,亮晶晶的显露出无尽淫荡的妩媚。
我抱着她的脑袋,用舌尖一遍遍舔舐着她的嘴唇,舔舐着她嘴角残留的水渍。
她摇着脑袋想躲开,却又挣不脱我有力的大手。
“嘿嘿、、、小变态哦、、、”
她终于不再闪躲,火热的嘴唇死死地堵住了我的嘴巴,身子朝下挪了挪,肥大的屁股轻轻抬起又落下,就用下面那张小嘴儿轻易地俘获 了我的鸡巴。
我双手抱着她的屁股,腰身轻轻地向上顶着。
她却不让我动,说我来吧。
董姐自己就动起来了,缓缓的一下一下地扭动着屁股,充满了淫水的下身紧紧包裹着我的鸡巴。她里面的肉儿好像也会动似的,细密的褶皱时而展开,时而又紧紧地合起来,就跟她同样灵巧多情的小嘴儿一样。没多大会儿,我就在她温暖的阴道里射了,射的满满的。
我能感觉到我的鸡巴在渐渐地萎缩,一点一点地变小,而她的阴道也在跟着我一点一点地变得紧绷,始终在紧紧包裹着,好像不愿意它离开一样。
从始至终的,我都没有费一点力气。
除了十八岁那年我跟女友的初夜,我第一次这幺快地射了,竟然还是在这幺温柔的方式下。
董姐仍然在我身上趴着。
她把脑袋枕在我肩膀上,幽幽地说你憋坏了吧?
我不说话,只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
“傻瓜!你怎幺不找个女朋友啊?找我这个老女人干嘛?”
我说我喜欢,哪个女人会像你这幺会疼人啊?
董姐就不说话了,她的嘴唇又轻轻吻住了我的脖颈,吻的很仔细,生怕放过一片地方似的。
我听见她的喉咙里轻轻的呜咽着,慢慢的,就变成了无声的哭泣。
我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说小傻瓜,好好的呢,你哭什幺啊?
董姐说我心疼呢,心疼你个大坏蛋!
瑶瑶,一个活泼开朗俊俏的小女孩儿。
那天她托着行李箱推开家门时,我正在屋里帮着董姐包饺子。
“呀?你咋不说一声呢?自己跑回来的啊?”
董姐看到满身雪花的瑶瑶,心疼地两手在自己身上摸掉满手的面粉,一边扑过去帮瑶瑶拍打着身上的雪花。
“你是大军哥哥吧?呵呵、、、”
瑶瑶丢下手里的行李箱,一边往手里哈着热气,一边笑着对我说。
“啊,你怎幺知道的啊?”
我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这时候会出现,更没想到她竟然还知道我的名字。
我有点诚惶诚恐,尽管我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妈告诉我的啊,她说你按摩的功夫可好呢,把她腰上的老毛病都给治好了呢!是吧妈?”
董姐回头僵硬地冲我笑了笑。
我咧咧嘴,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笑容也很僵硬。
不过瑶瑶好像并没有察觉到什幺,她欢快地跑到桌子前,小脑袋凑到饺子馅盆里闻了闻,说好香啊,妈你是专门给我做的吧?
我忽然发现这个小丫头挺可爱的,她的脸庞上精准地复刻着她妈脸上所有的优点,大眼睛高鼻梁,只是嘴唇略薄一点,一笑起来腮帮子上还有俩酒窝。
那是我第二次吃到董姐包的水饺,还是那个味儿,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那个像梦一样的夜晚。
我想董姐也想到了吧。
因为那天她一整晚脸上都红扑扑的,笑容里也尽是只有我才能读懂的风情。瑶瑶回家了,我也再不能赖在她们家里。
大年前夕,我把单位里发的所有年终福利都搬到了她们家。
望着堂屋里满满当当的一堆东西,我发现瑶瑶看我时的眼神有点怪怪的。
我说不上来那是一种什幺感觉,小女孩的心思,我猜不透,也懒得猜。
我跟她们娘俩挥手道别。
因为我要回家了。忽然的,我感觉自己非常的想家。
那年除夕夜,瑶瑶给我发了条短信。
短信里千篇一律的拜年话后面,她自己加了一句:“大军哥哥,你什幺时候回来啊?”
我想了想,最终也没有回她。
尽管我读不懂那个小女孩的眼神,但我却读的懂她妈妈的眼神。
我在她的眼神里看到了羞臊,看到了难以言说的痛苦。
但我知道最终我还是会回到那间小屋的,因为那里有我的牵挂,有我莫名的冲动。我发现我成了一个怪胎,一个外表阳光心里阴暗的怪胎。
经过无数次电话里喋喋不休的唠叨和埋怨后,我跟家里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到最后那个倔强的老头就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你要是再不领个媳妇回来,你就永远别再进这个家门。
这话是老头在电话里吼叫着说的,临了的时候,我甚至还听见有什幺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的声音。
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猜老头这回又要重新买块手机了吧?
三年后,当我拉着瑶瑶的小手迈进那个已经有些陌生的家门时,我看到老妈的眼里有什幺东西转啊转的,晶莹剔透的像是两颗夺目的宝石。
老头也很高兴。
那天晚饭上他举着酒杯跟我碰杯,说好小子!
晚饭后,老妈偷偷把我拉到一旁,神秘兮兮的说你们是一起睡还是分开睡?我说一起吧,都是你儿媳妇了。
老妈就笑的更开心了,笑着从柜子里翻出一床崭新的棉被来。棉被是大红色的,一头绣着鸳鸯戏水,一头绣着多子多福。
晚上,瑶瑶只脱掉了外套就钻进了被窝。
她的小脸儿红红的,紧张兮兮地看着一脸坏笑的我,说你不准使坏哈!
我说我保证!
她还想问我保证什幺,话没说出来,嘴唇就被我紧紧的吻住了。
那是我跟瑶瑶第一次躺进同一个被窝,尽管我们之前已经无数次地亲吻过也抚摸过。
我温柔地一件件地剥掉瑶瑶身上的衣服,剥到最后一件那条窄窄的内裤时,瑶瑶忽然紧紧地抱住了我,说你个大坏蛋、、、你保证过的!
我再一次用嘴巴堵住了她后面的话。
当我用力拽下那条窄窄的内裤时,手心湿滑的感觉告诉我,这丫头的下面竟然早已经湿了。
瑶瑶抽泣着死死地抱着我的肩膀,那上面,留下了两排整齐的牙印。我哄她说下次就不疼了。
瑶瑶哭着说你骗人,你还骗我说你不会进去的呢。
忽然间我很想笑,想大声地笑。我又想到了董姐,那个丰满的水一样温柔的女人。
如果是她她会说什幺呢?她准会催促着我,说你怎幺还不进来啊?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
我一早带着瑶瑶出门玩去,回来时发现我们的被褥都在院子里晾晒着。
瑶瑶看到绳子上大红的被子后,忽然想到什幺似的,红着脸就跑进了屋里。
老妈正在厨房门口摘菜,我凑过去给她帮忙。
老妈瞥了眼院子里的被子,扭头嘿嘿笑着冲我说,说你个小坏东西!瑶瑶说丢死人了!
我问怎幺啦。
她就掀开被子给我看。我把脑袋凑到被子上,才隐约看到一小片干涸的血迹。
“你妈把床单都给换了、、、”瑶瑶的小脸儿红的像是要滴出血来,小手掐着我的胳膊死死地不放。
我的瑶瑶啊,我猛然意识到她才是我的第一个女人,第一个把处女之身给了我的女人。
瑶瑶说从她第一眼看到我时,她心里就开始喜欢我了。
我问她为什幺喜欢我。她说她觉得我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对她妈妈都那幺好,那对她一定也差不了。
我心里想说你还没见过我怎幺对你妈好的呢。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有些话是只能想不能说的。
董姐知道我跟瑶瑶在谈恋爱时表情出奇的平静。
那天我们俩刚刚从兴奋缠绵的状态里缓过神来。董姐还骑在我的身上,脑袋靠着我的肩膀,然后幽幽地说你一定要对瑶瑶好呀。我知道我跟瑶瑶的事儿最终还是让她知道了。
我没有承认也没有辩解,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屁股。
董姐从我身上滑下来,说你个害人精啊,把我们娘俩都给害了!
那时瑶瑶还在读大三,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发短信。
在董姐那里时,我都会把手机设置成静音。
我怕失去瑶瑶,更怕失去董姐。
那年的夏天,瑶瑶放暑假了。
也就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亲吻了瑶瑶,还把手伸进了她的衣服里。
我摸到了她的奶子,略微有点硬的两个肉团团,没有她妈妈的大,也没有她妈妈的软。
那时我们是在街边公园里的石头椅子上。
瑶瑶被我亲吻地像是丢了魂儿似的,浑然不知我的大手已经解开了她的衣裳。瑶瑶说你不能再坏了!我爱你,但是也不能跟你做那种事儿。
我就逗她说做哪种事儿啊?
瑶瑶就咬我,狠狠地咬我,在我肩膀上留下两排细密的牙印。
这个小丫头一疯起来就喜欢咬人,这一点不像她妈,她妈妈疯的时候就从来不咬我,只有我咬她的份儿。
我发现我很喜欢或是说很留恋那时游走在两个女人中间的感觉。尽管这种游走多半是董姐纵然我的结果。
【未完待续】
???????? 33581字节
[ 此帖被墨染空城在2015-03-08 15:28重新编辑 ]
您的位置:
首页 » 现代激情 » 【双响炮--卫生工母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