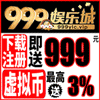第一章凤鸣
晋年间,征战四起,兵挣连连,凡军事所过之地皆刮地三尺,无论权贵、富商或平民,统统饱受煎熬。中州卞城两年易三主,原本的繁华街道已成冷巷,家家户户早早落门关窗,以避苛税和征召。
卞城西北角有一四合院,高树流水,亭台挂角,应是一大户人家。但看门庭冷落,久无修葺,便知早家道中落,只有那院门前刷得还算光亮的写着「吕府」的门牌还危危地显示着昔日的显贵。吕家本是卞城贵胄,家主曾受封爵位,然而战事一起,吕家举力助战,却于洛州遭埋伏,全军覆没。吕家家主吕诚宪得知消息一病不起,三月后离世。现吕家只剩下自小体弱的幼子吕衡与母亲及三两伺服,再无复世家之景象。可喜的是,吕衡两个月前与指腹为婚的赵氏完了婚,兼到卞城城西书院执任说书先生,在这战乱时期,还能勉强混日子过活。赵氏本名赵若,在卞城小有艳名,本家以州通贸易运商,也算大富大贵之家,然而卞城易主,便遭到肆虐搜刮,大量家财被充军,庆幸并无伤着家眷。赵家本以为能破财挡灾,岂知卞城两年易三主,不只征银、征粮,甚至稍为青壮点的男丁,都全部被征走,赵家家主见儿子受征,唤起家丁反抗,是夜便遭火烧家园,只有一家丁携着赵若投奔吕家。吕衡虽和赵若有婚约,然而赵若投奔吕府当天两人才第一次相见,当时便被赵若姿色所迷,惊为天人,虽处战乱世代,艰难与其完婚。在这凄惨时节,这婚事却给卞城徒添一笔生气。
秋风送寒,日上门楣,吕府西厢房中,一女子正在给吕衡穿衣弄戴,而她本身却只披一卷薄纱,半透明的薄纱根本掩盖不住赵若如缎似丝般的肌肤,那漆黑柔顺如瀑布般的长发直抵其丰臀,衬托着她那柳絮般的小蛮腰,阳光散落在她的身上,映照出万般绮丽,不可逼视。赵若全身红潮欲退,显然刚亨鱼水欢愉,带着满脸春意小心翼翼地为其夫君细心服务,此女子便是赵家遗孤。吕衡站得笔直,接受着妻子温柔的双手为其服务。而他的双眼一眨不眨的盯妻子玉容,只觉盈盈然不可方物,感叹苍天之鬼斧神工,把天下一切美好的、绮丽的,炫目的、优雅的特质都雕刻在了妻子的脸上。吕衡的眼神自面容徐徐往下下滑,滑过那不堪一握的玉颈,再滑过那纤细光滑的臂膀,越过那勾魂荡魄深沟乳壑,到达那粉嫩蜜桃般的乳房,目光最后定格在乳房上的那两点凝滋玉露般的蓓蕾上,便再也移不开眼了。从初见赵若时到现在完婚两月,吕衡仍然不可相信眼前佳人竟然是自己最亲密的妻子。自战事开始,他遇上的无不是令其绝望恐惧,不可入眠的遭遇,在最活不下去的时候,竟然遇上赵若,怎不让吕衡觉得自己如入梦中,不可置信。
他还记得初遇赵若的惊艳,记得成婚当晚,初见赵若胴体时那离魂般的悸动,记得赵若破身时疼痛难忍的容颜和那惊心的落红……一切都如在梦中。
「夫,夫君!」天籁般的声音响起,又甜,又腻,彷如仙乐。
「啊……」吕衡才回过神,支支吾吾的应道,但是目光始终不离那对乳房。
「夫君你……夫君……不好整理了」语毕,赵若本来已将尽退的红潮又再度升起。
原来吕衡在恍惚间已伸出两根手指在赵若的腿间,贴着她的嫩缝不断地来回摩挲,如此动作挑拨至极,就算是夫妻,光天白日下施展也是羞愧难当。吕衡立马把手收回来,又端正起来,暗自责备自己才刚刚发泄完,怎幺这幺快就忍不住,惹得妻子难为,又道妻子美若天仙,咋就这幺好运给自己遇上云云。而女子继续认认真真的帮吕衡系好腰带,由于需稍微用力,身子便轻轻一斜,也不知道是缎带太细滑,还是女子的肌肤太稚嫩,身上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得薄纱就顺着身子滑落。这一幕落在吕衡眼里,脑袋一冲,一泉血柱就从鼻腔留下来。
女子盈盈一笑,捡起案旁的丝帕帮吕衡抹去鼻血,轻道:「相公需小心保重,切莫伤了身体。」吕衡又觉如梦如幻,唯唯诺诺,也不知是怎幺走出房门的。
女子把吕衡送出门外,脸上的温柔尔雅立刻消失,随之换上了一脸冰寒,不顾那落地薄纱,右手伸自虚空一抓,便凭空抓出来一个秃顶散发的老者往墙壁一按,「轰」的一声巨响,那老者还来不及呼疼叫痛,一只如春竹般玉腿往前一伸,纤足印在老者散落在墙壁的头发上,拉扯着老人让其不至跌坐。女子本就身无寸缕,这样把双腿一分,右腿高高抬起,便把玉户肉缝毫无遮掩的呈现在老人的眼前,她本身却好像对此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冷冷的望着老者。
「可……可儿师妹,您请息怒,我赔罪,赔罪行吗?」老者嘴上说赔罪,可脸上哪有赔罪之意,愣愣的盯着女子的肉缝,口水「滴答滴答」漏出嘴边,时而还伸出几近一尺的细长舌头舔着口唇,分明一副色鬼淫相。他那已秃了大半边,零零散散的头发正被他口中的可儿师妹踩住,挪不开头,也不想挪,双眼正好与女子肉缝持平,正大饱一顿眼福。
「什幺时候开始偷看的」女子冷冷的说。
「从您那病鬼丈夫一睁眼就想屌您开始。」「可好看?」「师妹您好看,那病鬼就太没看头了,才几下就泄了,如果换了是我…哎哟哟,别印别印,没几根头发了,哎哟哟…」「我叫你以后还看!」女子看见老者头发又掉了几束,才稍微放松一点,单脚还印在墙上,一点放开的意思都没有。
「不敢,不敢」老者扣上说不敢,可心里转着就算头上这头发都掉光了还是能看就一定不错过的念头。
「来找我什幺事?」女子说「我最近在城里溜达,偶尔看见了轻音门的人时常在卞城走动,上几天还发现音仙子到了城南,像在寻找东西,我给您说一声,提防提防,可别让人发现了凤鸣石的所在」提及凤鸣石,老者倒是正经了几分,可是眼光依然没离开过那条肉缝,仿佛就是对着肉缝说话一样。
女子对他这番模样倒是习以为常,面不改色,只是听到「音仙子」,略显惊讶:「羽音那丫头也到了?」「嗯。」女子口中的羽音便是那所谓的音仙子,是轻音门新一代年轻弟子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原来女子本不是赵若,而是葵月门最杰出的女弟子纪可儿,老者则是她的同门师兄阴魁,生得蛇头鼠眼,脑袋秃了半边,余发胡乱的交缠在一起,模样丑陋不已。葵月门属修道门派,因其道门最高道法凤鸣决能召唤神兽朱雀下届,因此在诸多道门中也属顶尖儿的派别。然而修炼凤鸣决条件极其苛刻,葵月门苦寻三十载才找到纪可儿,不但修道天赋过人,又生的精致优美,甚得师门长老疼爱。而她也不负门人厚望,入门五载便初步掌握凤鸣决,但因为修炼此决必须以满盈地脉灵气的凤鸣石以辅助,所以纪可儿每隔一段时间必携着凤鸣石寻找神州各处地穴吸纳地脉灵气,直至凤鸣石达到满盈状态,方可回师门修炼。本来采集地脉灵气,找个门下弟子小心进行就好,但入世也是修道的一部分,因此大部分时候却是纪可儿亲自下山。此次发现汴城中央的地脉灵穴,便隐匿城中,恰逢遇上赵家惨变,就借赵若之名,隐于吕府,成了吕衡的妻子。她天生丽质,又自小养成温文尔雅的气质,直把那吕衡迷得神魂颠倒,本来就体弱的吕衡,自成婚后必与纪可儿每日交合,不能自已,甚至一宿三五次,完事后见纪可儿春颜,又忍耐不住,然则不能举了,便彻夜抚摸摆弄纪可儿身体,无一寸肌肤遗留,彻夜不眠。奇怪的是,纪可儿虽身负神通,却对吕衡的予索予求极尽满足,任其折腾,直把始终隐没在旁的阴魁气得三花聚顶,淫火烧心。两月间吕衡身体愈见衰弱却不自知,整日如堕梦中。观其气息,如此继续下去,怕过不了年关。
纪可儿如是沉思半刻,又道:「凤鸣石还得再三天方可盈满,而且凤鸣石向来是我派最高机密,轻音的人想必不会知情,她们此行该不会因我派而来,或许这卞城,有其他什幺我们还未发现的情况,你下去无论如何得给我查出来。」语毕,见久无回应,便微转目光望向前方。只见阴魁望着自己美妙的玉户在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秃顶上已见汗滴渗出,纪可儿便知阴魁已情不可控。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只是轻轻地从樱唇吐了口气,如兰似麝,一声轻笑:「嘿」阴魁如被触电,尽管双眼自始至终未离开过那条迷彩幻离般的肉缝,但迷离的眼神渐渐聚拢,已回复几分神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师…师妹…您那嫩痕外透晶莹,还…还有您那病鬼丈夫刚射进您体内的精液渗了出来了,您…您…您…」阴魁边说边抬手向玉户伸过去,奈何他天生就比别人矮小,他那拙手就算伸的笔直,也够不着玉户,尽管拼尽了力,也只能在纪可儿修长的大腿间乱晃。
见此情形,纪可儿微微一笑,她明知吕衡刚向她的小穴泄了阳精,而刚才抓人伸腿的动作是大了点,势必使体内的精液受动作影响挤迫出来,溅到阴唇边上,可她就是想折腾折腾这位师兄,特意让他看到这种情景却又不让他碰着。面对这在自己大腿间乱武双手的老者,纪可儿终于忍不住,放声媚笑起来。
「师兄可真是妙语,竟能把阴缝小穴说成嫩痕,可是雅致的很呀!」声音如春风带笑,媚入骨髓,诱人之极。
「这可都是师门对可儿师妹您那小阴户的一致评价啊!粉肉不显肥,娇小敛于内,清溪狭洞,迂回九曲,吸缠蠕振,如肉蚌鲜嫩,若春雨留痕——是为嫩痕」「呵呵…我还真不知道师长兄弟门给我那小小肉隙的大大评价,嫩痕,嫩痕…」纪可儿边重复着「嫩痕」边往自己腿间望去,犹似在验证这刚听见的新名词一样。此时阴魁已经青筋覆脸,眼内红丝欲裂,下体伟壮之物涨衣伸出,已成金刚铁柱。
纪可儿知道再如此下去,阴魁必蛋破茎裂,身死道消。于是再不挑逗,说:
「那师兄可否为妹子理净一下玉户…哦…是嫩痕!」纪可儿双眼一眯,妩媚地望向阴魁。
阴魁双目几欲喷火,大喜过望,连声:「万般荣幸!万般荣幸啊!师妹意思是从我了?」纪可儿点了点头,说:「别忘了规矩!」听见最后「规矩」两字,阴魁再也不可忍耐,横生一股大力,和身撞入纪可儿怀里,把如蛇如鼠的脸塞进那迷人深邃的乳沟里。两人紧贴着离地后仰,尚在空中,纪可儿双乳已被阴魁那长舌卷住,变换出各种形状,同时又留下一圈圈水沫,转眼间漫满了双乳,想必便是口水唾液。而阴魁不知何时竟已从腰间抽出捆仙索,把双手自绑在一起置于胯间,动作迅速异常,也不知需多少次的重复运使才能做到如此纯熟。待得两人跌落软床时,阴魁已把纪可儿的右边乳房纳入口中进行着撕磨噬咬,唾沫于牙缝里不住往外飞溅,滋滋有声。而最其怪的事,他一边噬咬着纪可儿右边的乳房,舌头却伸到左边的乳房上,寻上那玉露蓓蕾,先在乳荤上乱捣数圈,接着舌尖从中凹陷,变成小嘴形状狠狠抵住乳头,抓捏着,左摇右咬,如暴风骤雨。与自绑在胯间静静地一动不动,虽离纪可儿的「嫩痕」不过几寸,却不曾向前探去的双手形成强烈的对比。
阴魁状若疯狂,动作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力,几可让身前的肉体留下淤痕。
而承受着这一切的纪可儿则像个木头人一般,看着阴魁在自己身上任意施为,只当是衣履盖身,甚无兴致。良久,她渐觉无趣,终于忍不住开口叱言:「你咋的不往我腿间舔去,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嫩痕吗?进去捣乱啊,你以为舔我双乳会让我觉得有意思吗?」音魁听罢全身一震,依言放开其双乳,向娇躯下方移去。纪可儿也适当地张开双腿,把那无限美妙的肉缝裸现出来。双腿一张,尽见风光。诱靡的小腹下端滋长着鹅绒般的阴毛,虽不浓密,然而疏落整齐。里间肉缝鲜嫩粉红,光滑若水,不带杂色,娇小甜美,形状犹如仙子樱唇,盈盈浅笑,望去让人感觉如沐春风,玉洁清纯。实比「如肉蚌鲜嫩,若春雨留痕」犹有过之,不可言喻。且见肉缝间晶莹淫液混和着虚白阳精缓缓地被挤出,青涩中更添一抹淫亵。
尽管阴魁看这阴户外唇已无数次,却依然不可歇止被其所迷,舌头也忘记收回嘴里,便就在离阴唇二指处呆住,连唾液都干涸了。直至一双滑腻如丝的春竹玉腿圈住了他的颈项,把他硬推至阴唇上,嘴脸都掐进肉洞里才牟然醒觉,口齿不清地说着每次此情此景都会被勾魂夺魄等等。
然而纪可儿根本不理会他的赞美言语,只冷哼道:「把你的舌头塞进去,不捣个天翻地覆,看我以后还从你不?」阴魁想都不想,便把舌头伸进肉洞里,和着淫液与阳精滚旋不已。不得不说阴魁这舌头确实天生异品,细长而灵动,各种卷曲拉伸不说,还能如臂使唤。自进入纪可儿肉洞后,便在洞内翻云覆雨,时而高速转动,摩挲肉壁;时而折叠变粗,进行冲刺;时而又直捣黄龙,进到肉洞深处,咬住她的子宫进行瘙痒吞吐。
至此,纪可儿面上的冰冷才尽数退去,给无限的欢愉、兴奋、欲求所完全替代。
娇洁的面容时而媚笑,时而痛苦,时而又显欲求不足,阵阵浪叫、吆喝蔓延至闺房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她那天籁般呻吟声的,是肉穴里的大量淫水,每一次呻吟,淫水便想翻一次波浪,床上软枕,锦被均都得到了纪可儿的滋润。
「啊………嗯………哦哦哦………往左边点,痒…。啊……深点,到顶了…咬住……对了…啊……」呻吟渐渐变成淫叫,随着深入程度越高,纪可儿的表情越接近高峰,她此时已全身红潮涌动,美艳不可方物。双腿深深往里面用力,纤腰却使力外顶,一次次迎合着双腿的振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要来了……」随着一声高吭,纪可儿终于攀上了巅峰,这时她方放软双腿,左右软摊在床上,才见满面青色的阴魁露出面来,一半舌头仍插在玉户上,人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气。原来方才纪可儿淫欢过愈,竟把阴魁堵死于肉洞内,而肉洞又淫水泛滥,根本无法呼吸,至令阴魁差点窒息在阴道里。幸亏他乃修道之人,气息远比常人悠长,又明知不能满足纪可儿,便无法脱困,是已尽显所能让纪可儿尽早泄了阴精,方有脱危之机。此番果然奏效,只是阴魁面上已斑斓一片,不知是淫水,是阳精,还是纪可儿的阴精,反正已混为一体花花绿绿,不可分辨。
然而阴魁回气过后,红潮从攀全身,竟未泄阳。此际惊魂甫定欲念回涌,竟不可遏制。他理智全失,光芒一闪竟挣断捆仙索,双掌向纪可儿胸部袭去,掌握住两对玉乳,腰身往上一挺正欲攻城略池。正当玉龟顶开阴唇,半进未进之际,颈上传来了一丝冰凉。
「敢进去,我就一剑毙了你」阴魁回醒过来,见纪可儿手握仙剑,搁在自己颈旁,森然杀气溢出,态度无可置疑。
然而阴魁已半根肉棒进了阴道,感受着肉壁的片片压迫感和融融暖意,眼神露出深深不忿,咆哮道:「为什幺,为什幺你从来就肯不给我。你可以给师傅,给师叔,给那病鬼吕衡,甚至可以给门里的那个烧柴的,而我每次每次都只能自绑双手,俯首给你舔净阴道污秽,连摸摸你都不行,为什幺?」阴魁越说越用力,全然不知纪可儿双乳已经给他捏出了淤痕。
纪可儿对于阴魁的咆哮不予理会,只看着被他捏得扭曲变形的双乳,看那渐渐浮现的淤痕,目光冰冷,淡淡地道:「这幺说,你是连给我舔阴道的活儿也不想干了?」阴魁听罢全身剧震,望了望纪可儿和自己,颤抖着缩回双手,把龙根缓缓抽离阴道,像犯了弥天大祸的小孩子般呆在纪可儿床头,双眼已湿润,却不知是悔意,抑或是委屈。
纪可儿此时才缓缓地移离仙剑,往阴魁下体看去,见其龙根依然挺拔如柱,膨胀欲裂,轻舒了一口气,收起冰冷的目光,像只小猫般的爬到阴魁胯间,张开玲珑小嘴,向那铁棒般的肉柱含去,悉心套弄。直到大量阳精泄进她的口里,方含着阳精抬头望向阴魁。由于液量过多,不少精液自纪可儿口中挤迫而出,却见她一皱眉,便把精液全数吞入腹中。站起,穿衣,离房,就像什幺事也没发生一样。
然而阴魁意识到,下一次尽管纪可儿不一剑斩下,自己也必然道心破毁,身死魂灭。他呆坐床头直到日已中天,才心有余悸向房门外方向望去,心知纪可儿道行已精深到举手投足间便能破其道心,夺其性命,顿感惊栗不已。
吕府西厢房内一番动静,绵绵呻吟,阵阵咆哮,全府竟无人得觉。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棋牌游戏
官方葡京
PG大赢家
澳门葡京
太阳城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新葡京
澳门葡京
PG娱乐城
PG大满贯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PG娱乐城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PG国际
开元棋牌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
免费呦呦破解